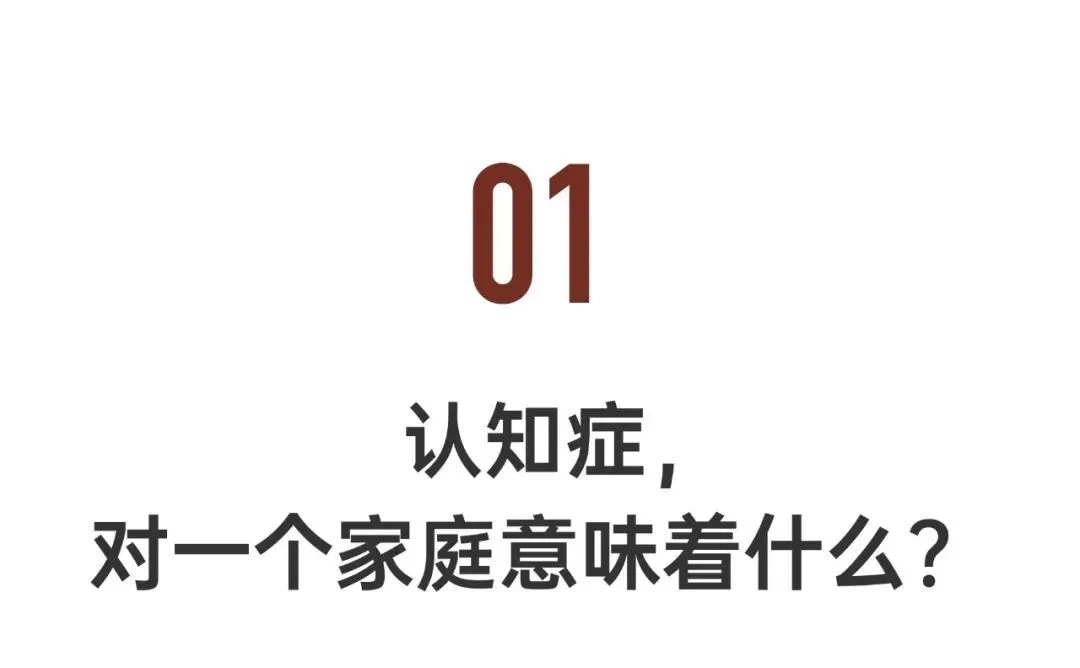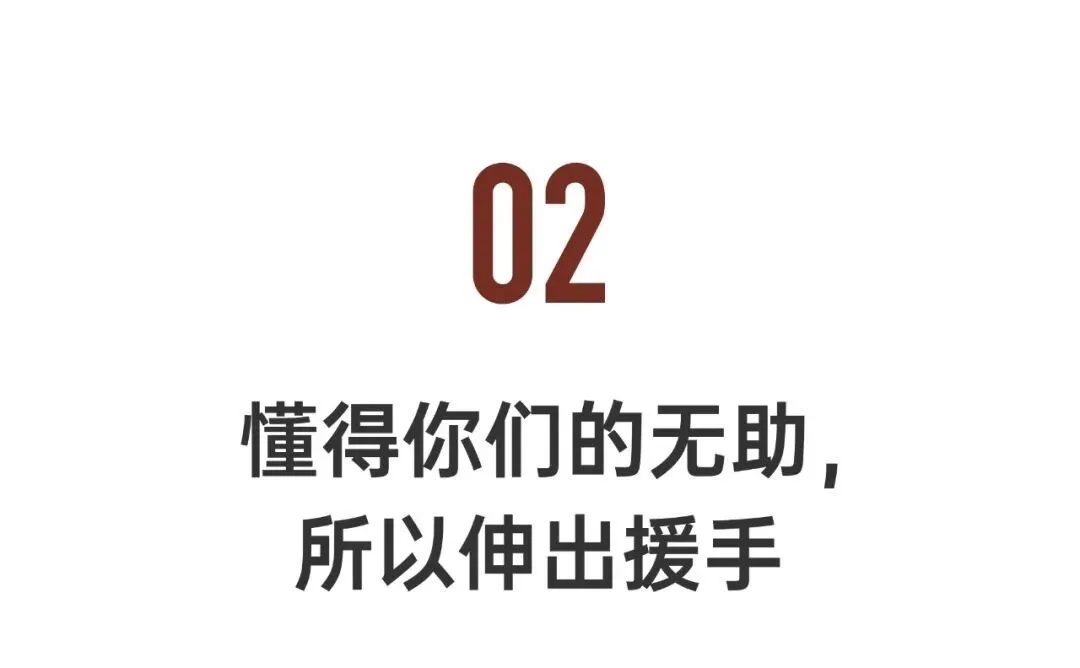阿尔茨海默病,是许多人对于变老最大的恐惧之一。它意味着失去记忆、情绪异常,最终导致认知的全面衰退。而阿尔茨海默病,只是认知障碍中最常见的一种。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,我国现有阿尔茨海默及其他认知症患者近1700万,占全球总数近30%,而许多人对认知症及其照护仍缺乏基本了解。纪录片导演任长箴和周轶君一起,将镜头对准认知症老人以及他们的照护者,展现他们面临的困境、挑战,以及希望。这不是一部关于“失去”的记录,更是一次关于“存在”的追问:当记忆的坐标被模糊,一个人何以确认自己,爱又将以何种方式存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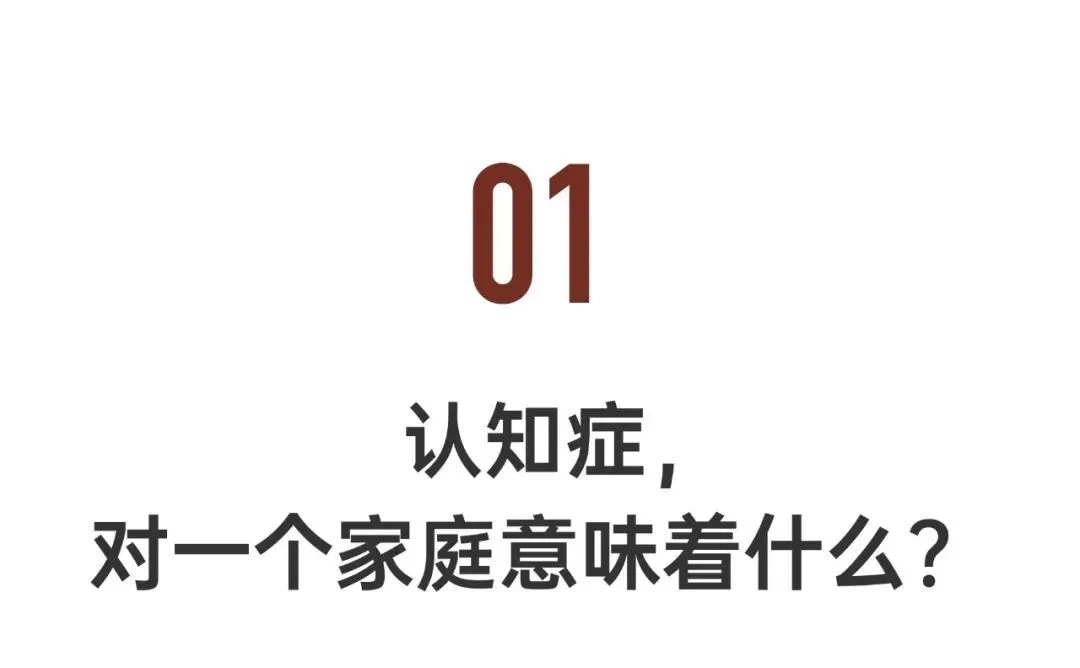
纪录片的开头,周轶君问了老人们三个问题:“您多大年纪?”“早饭吃了什么?”“您有几个孩子?”

这些对常人来说最简单的问题,却无法得到哪怕一个正确回答。老人中有曾经大学的教授、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、野战部队的军医……但认知症带走了他们的记忆、语言与表达能力。他们遗忘自己的年龄,不记得早上吃过什么,长时间地徘徊在头脑中那个扭曲的世界。
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,认知症是由多种影响大脑的疾病引起的一种慢性或进行性综合征。世界上每3秒就会有一人被诊断为认知症,表现出记忆、语言、行为障碍,乃至激越行为:多疑、妄想、刻板的行为重复、语言和躯体的攻击……背后,则是他们对自我被剥夺的巨大恐惧。

同样被剥夺的,还有他们与家人之间的情感纽带。
宁宁今年53岁,她的母亲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8年。将近3000个日夜,她随时陪护在母亲身边:做饭、喂饭、打扫卫生、为母亲按摩、清洁身体、陪她散步……时间与体力的巨大消耗之外,更让她崩溃的是无法从母亲那里得到正向的情感反馈:“我觉得我无论怎么做,都无法让她满意。你越是想让她过得好一点儿,你越难。”

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,远非准备一日三餐那么简单。社交媒体上,时常能看到认知症老人的家属们表达心酸和疲惫:
“体力上精神上的彻底崩溃”;
“爷爷以前脾气特别好,生病之后就变了,骂人、尿床、抹屎,感觉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”;
“保姆护工换了好几个,顶不住他打人骂人,感觉自己24小时生活在抑郁里,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”……
认知的衰退,重塑了老人的心智和人格,也让长期照护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梦魇中。纪录片的镜头前,宁宁哭着对母亲说:“妈,我也50多岁了,我也没有几年活头儿了,你让我有点儿自己的时间,行不行?”

心力交瘁的时刻,宁宁也考虑过让专业机构来照顾母亲,但顾虑重重。长久以来,“送父母去养老院”似乎与“不孝顺”划上了等号,这让很多人即使有想法,也迫于外界压力最终放弃;另一方面,经济上的压力也无法忽视。
在我国,大部分认知症患者仍由家人负责照护。根据国内首个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生存状况调研报告》,65.43%照护者看不到治疗希望,感到心理压力大;68.69%的照护者健康受到影响;78.39%的照护者的社交生活受到影响。无尽的委屈和无力感、频繁的焦虑与恐慌、个人时间的彻底剥夺……长期照护认知症老人的压力就像是一个不断被积压的气球,时刻在爆炸的边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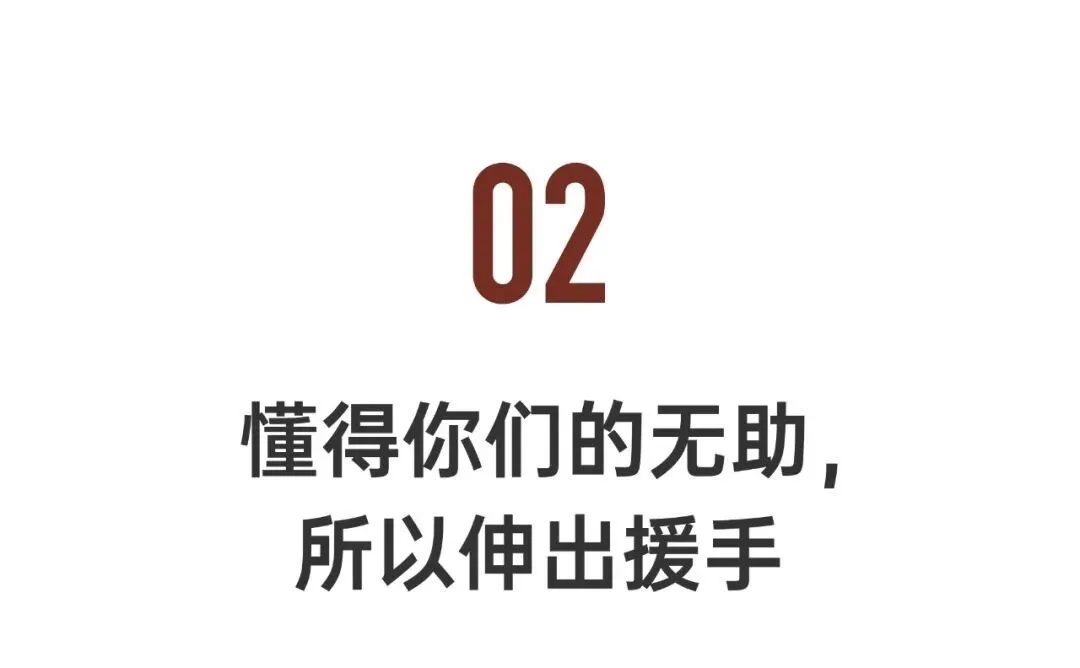
卫正霞25岁,在“记忆照护区”工作,负责照护的都是患有认知症的老人。她记得有一天中午,她和同事们去查房,还没走到门口就闻到臭味,推门进去后发现房间的墙上被涂满了粪便。她笑着说:“当时我感觉天都塌了。”
几乎每一个护理师都有过类似的经历,甚至有老人会把粪便直接扔到他们的身上。更不必说时常发生的激越行为:妄想发作、言语辱骂、肢体攻击……
有时候,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会问自己:为什么我要选这个行业?一个大学生,做这种又吃苦,又脏又累的活?

22岁的护理师王悦,一度考虑过退出。最纠结的时候,她给父母打了电话,父亲这么说:“如果你自己都不认可自己的工作,谁还会认可你们这个行业?”她一下子被触动了:“那我就再试试。”
成为护理师的过程,也是与老人们建立情感联结的过程。王悦至今都记得自己曾经照顾过的一位顾阿姨,那段时间她很想家,就在闲谈中和顾阿姨提起,顾阿姨说:“我抱抱你啊”。
“我一下子觉得特别温暖。当你熟悉了每一位老人之后,会觉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好,都很可爱。有的时候他们是会打你,不理解你,但他们只是生病了。”她说。

支撑这群年轻人投入照护事业的,不止是一颗热忱之心,更是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专业培训。入行之初,他们会接受一次特殊训练,穿上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特别研发的拟态服:眼镜片只留一个圆孔,模拟老人狭窄的视野;耳机让人听力模糊;厚重的手套让手指无法弯曲;沙袋束缚住手腕、脚踝和膝盖,感受行动时的沉重……
拟态服的正式名称是“衰老移情系统”,穿上它,哪怕只是走上几步,都会让人汗流浃背,疲惫不已。理解这些老人的无助,是护理师真正走近他们的第一步。

真正的帮助,是感同身受后伸出的援手。王悦每天走进病房的第一件事,是笑着向记忆衰退的阿姨重新介绍自己;另一位护理师青香,会和老人下象棋、陪他们看新闻、做早操;照护主管金红,在看到吴奶奶激越发作,错把摄影师当成坏人后,没有反驳和敷衍,而是耐心真诚地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解决……
很多时刻,认知症老人需要的不是纠正和规训,而是认可和理解。不揭穿他们的错误,不纠正他们的胡话,照护不是给予怜悯,而是郑重对待。
日常照护之外,护理师还会使用非药物疗法,如重现过往场景的怀旧疗法,来延缓老人认知功能的衰退,帮助他们重新唤醒对自我的认知。

曹泽玺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空军飞行员,某天,他参加了一场特殊的“人生报告会”。一切都像模像样:讲台、红旗、坐在台下认真聆听的观众们……尽管老兵曹泽玺已记不清早餐的味道,但当他戴上勋章,讲述着脑海中模糊不清的人生往事,仿佛有那么一刻,他真的回到过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。

衰老和疾病或许可以模糊一个人的记忆,但照护者们相信,它们无法湮灭一个人存在的价值。在他们眼中,老人们是一个个真实、鲜活的个体:刘院长挥挥手是想喝水了,李奶奶每晚八点要和儿子视频,肖奶奶睡觉前要在床头摆好小兔子……用真心承托起这些暮年灵魂的过程中,照护者们也得到了疗愈与共情;当记忆模糊之后,爱的信标反而愈加明亮。
在纪录片的末尾,护理师高欣这么说:“我们现在的工作,它好像不是‘工作’,我们的对象是生命,是用生命去陪伴生命。”

2024年,任长箴与周轶君一起,拍摄了纪录片《学会老》,用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重新定义“老年”。但伴随老年生活的不总是健康与活力,如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认知症就是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。目前,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中有超过5300万患有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,但关于这一疾病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、如何影响家庭、怎样才是正确合理的照护方式……大众还了解得太少。而了解,始终是改变的第一步。
这也是任长箴与周轶君再次携手,花费一年时间拍摄这支纪录片《陪你老》的原因。
任长箴说,在拍摄之前,她对老年护理的刻板印象是一群50岁以上、文化程度不高的护工每天给老人喂饭喂水;但真正接触后,才发现专业照护要做到的远远更多。音乐疗法、怀旧疗法、记忆训练……在身体的照料之外,护理师会通过各种非药物疗法来缓解老人的身心压力。为了照护认知症老人,新员工要接受入职8小时导入培训,培训合格之后才能进到记忆照护区。之后3个月、6个月内还有30个小时能力提升的培训,再接下来还有50个小时的专家级的认证和培训。这不仅是为了提升专业技能,也是保障护理师们能获得心理上的指导和支持。

“我也和认知症老人的家属交流过,有位女士的母亲2018年开始出现症状,当时家里四个人一起照顾,但她说自己的内心还是只有‘崩溃’两个字可以形容。送母亲到专业机构后快7年了,状态非常好,她很感激护理师能让母亲在患病的同时还保有尊严和欢乐,这是她光靠爱做不到的。”任长箴说。
纪录片的最后,宁宁决定把母亲送到养老机构,让她得到专业照护的同时,也给自己“松绑”。未来,这可能成为更多认知症老人家庭共同的选择。当照护的压力无法在家庭内部被消化,向外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,对照护双方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

认知障碍不只是个人、家庭,更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,它关系着每一个人后半程的生命质量。学会直面这份恐惧,接受、了解、提前规划,在需要时寻求专业层面的照护,我们或许无法改变患病的事实,却能让这场旅程变得更轻盈、坦然。
正如周轶君在纪录片里说的那样:“照顾认知症老人,就像是捂一盏快灭的油灯,每个人都知道,它不会再亮起来,但只要全心全意护住那点小小的火苗,就能温暖地走完最后一程。”